- 钢绞线多少_天津瑞通预应力钢绞线 > 产品中心 >
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胡兰成往事:一段跨越时空的交往记忆
2026-01-09 12:24:18 118

我并非胡兰成的至交,尽管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但交往并不频繁,彼此的了解也颇为有限。然而,在195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期,当胡兰成如同老马伏枥,蛰居东京之际,我恰巧在东京担任台北《中央日报》的驻日特派员。在朋友的引荐下,我们得以相识。
昔日,他对我过于信赖,误以为我在台湾政坛与文坛的人际关系颇为厚,能助他于此地安顿并拓展事业。因此,他并未掩饰意图,屡次主动与我接触。
起初,鉴于他的背景与过往经历,我心中存有一丝警惕。然而,随着交往的入,我渐渐发现,他实则是一位文采斐然、颇具魅力且并不令人反感的个体。因此,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格外融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随着时间的移,或许是他察觉到我的能力有限,不足以协助他来台,我们之间的关系便逐渐变得疏离。
自与他中断联系之后,漫长的时日悄然流逝,直至台湾的朋友传来消息,方知胡兰成已迁往宝岛,于学府之中授课,并出版了数部引起轰动之作。
我心中为他感到欣慰,然而,不久之后,却听闻他不幸被“逐出”台湾,转而赴香港,历经波折,终又回到了日本。
他与我失去了联系,我也未曾主动寻求他的音讯。直至他的噩耗,我方从日本报纸上得知。
青年胡兰成
初将我与他的相识介绍给我们的,是一位才情横溢、既能吟诗作画又精通无锡方言的香港友人,薛慧山先生。
大约在1962年的尾声或1963年的初春,薛老莅临东京,我通过电话邀请他共进晚餐,他欣然应允,并表示将携一位定使我“相见恨晚”的朋友一同前来。我原本以为这位朋友是与他一同从香港而来的,于是毫不犹豫地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当他们如约踏入餐厅,与薛老同行的是一位身穿中国式缎面丝绵袍、肤黝黑、清瘦的老者。那件棉袍略显陈旧,而老者的面容虽不显饥,却毫无生气。我的一印象仿佛是一位历经历史巨变后流落至香港的失意文人。
薛老先行一步,轻轻挥手,介绍道:“胡兰成,我的这位老友。”
听闻胡兰成的名字,我心中不禁一震,凝视着眼前这位长者,我并未如薛老所描述的感受到“相见恨晚”的喜悦,反而更多地涌动着惊愕与失望之情。
我与众多读者无异,皆因阅读张玲的著作,对其小说情有钟,方始知晓胡兰成其人。
张玲
我于1950年代末被报社派驻东京,到后不久,就听说“汪伪政权”时代在南京做过官的许多“汉奸”,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都逃到日本来了,胡兰成是其中之一。
颇让人好奇的是,当东京的侨界朋友们在谈及同侪或相关事宜时,胡兰成这个名字总会被提及,然而,他们所谈论的,无一例外地,都是他过往的往事,而鲜少有人关心他的当下生活。人们普遍测,他可能是隐居起来,来东京安度晚年了。他似乎从未参与过侨界的任何公开活动,也未曾听闻他在侨界中拥有任何亲密交往的朋友。
他们或自“二战”前便长期居住在日本,或已入籍日本,成为了台籍的老一辈华侨。
“二战”后迁日的一代新侨,与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到日本的二代新侨,此中又混杂着暗获日本包庇的“汉奸”,或暗受日本支持的“台”分子。
此外,众多省籍的异地同乡会亦颇具影响力,诸如台湾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其中,“东京华侨总会”便存在两个同名机构,一派倾向台湾,位于银座;另一派则支持大陆,坐落于新桥。这两大会所相隔仅地下铁一站之遥,步行仅需十分钟。
在这纷繁复杂的华侨群体中,胡兰成因背景与身份的特别,其居简出的生活方式显得尤为可以理解。
若非薛慧山冒然将其引入我的聚餐之中,我恐怕至今仍无缘得见胡兰成,更遑论与之相识。
尽管直言不讳,若薛老在电话中事先告知,他将携胡兰成一同出席,纵然我无法预判自己是否真的会如同薛老所言,心生“相见恨晚”之感,但内心处,我对能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机缘,确实抱有一份期待。
我对胡兰成好奇。
他不仅赢得了才情出众的张玲的青睐,成为她的初恋情人和丈夫;同时,他也能宽容地接纳被称为“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的佘珍,甘愿在她的裙下俯称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若以张玲的视角来揣摩,胡兰成当是风度翩翩的俊雅文人;而若从佘珍的立场来考量,他恐怕不过是个粗俗不堪的平庸之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特征,竟如何能集于一人之身?
当然想见此人一面。
终,我们得以相见。然而,一眼望去,我竟感到了意外的失望。眼前的胡兰成,既非想象中那般风流倜傥、风度翩翩的白面书生,亦非粗俗不堪之辈。我的直观印象是:一位毫不起眼、显得颇为苍老的糟老头。
老年胡兰成
步入餐桌,我对他的印象渐渐好转。他格沉稳,寡言少语,目光锐利地扫视着薛慧山和我。薛老兴采烈地分享着他游历东南亚的种种见闻。
不知何时,谈话的焦点转移到了中国书画之上,这恰是薛老所长,我自感无从插言,而胡兰成却时不时地附和几句。
我静静地在一旁观察着他们两位,彼此年龄相仿,估计都在六十岁左右,薛老或许还要年长几岁。那时的我,仅三十六七岁,自觉与两位长者并非同一时代之人,因而未曾多加插言。
在那次聚餐中,令我难以忘怀的,便是胡兰成在分别之际,特意向我索要名片的一幕。
身为记者,我们从不吝啬递上自己的名片,然而在那日,我身为东道主,而他却是薛慧山引荐的嘉宾。他似乎摆出一倚老卖老的态度,并未主动递给我名片。我则故作淡然,并未回赠他名片。然而,当他终向我索要时,我还是给了他。尽管如此,他依旧没有回赠我名片。
约莫十日之后,我意外地接到胡兰成的来电,告知薛老即将返回香港。胡兰成表示,他将设宴为薛老践行,并热切邀请我一同前往,地点依然是那熟悉的中餐馆。我心想,这或许是他对上次相聚的回请。于是,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落座之后,他们之间几句简短的寒暄语引起了我的关注。薛老似乎在说:“何非得去餐馆饯行,您的‘珍嫂’烹饪手艺,可比此处胜出一筹。”
胡却注视着我,言道:“黄先生乃初次相识,岂能劳动您亲临寒舍?”
有机会,定来打扰。
胡却没有答话。
事实上,我衷心期盼他能说上一句“欢迎随时赐教”之类的客套,那时我便可以趁热打铁,询问他的住址。毕竟,对于“珍嫂”这位人物,我的好奇心愈发浓厚。
昔日在东京,提及胡兰成之名,便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佘珍。关于佘珍的传闻,甚至越了胡兰成,人们称她为“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传说她凶狠残忍,能够双手开枪,杀人如麻,“七十六号”一旦捕获女犯人,便交由她拷打审讯,非但命堪忧,更是皮开肉绽。尤其是她抵达东京后,竟与胡兰成结缘,这使得这对男女的传奇彩愈发浓厚。
若有机缘得以一睹这位人物的风采,我自当竭力争取。
胡兰成、佘珍一60年代
在那日的晚宴之上,胡兰成虽未明言对我造访表示欢迎,却巧妙地埋下了一枚期待未来交往的伏笔。他主动提起,曾在《中央日报》的航空版上阅读了我所撰写的通讯文章,对其颇感敬佩。紧接着,他表示自己也热衷于撰写文字,渴望能寄几篇杂文与我交流心得。我自然欣然表示愿意拜读,并恳请他尽快寄来。
果然,没过多久,他寄来了一摞文稿,其中既有杂志的精选本,也有手稿的影印件,内容以杂文为主,间或涉及日本政局的探讨。阅读过后,我感意外,不禁对他的文采赞叹不已,声予以赞赏。
特别是那些杂文,它们谈论人生、哲理,以及风花雪月,无不妙笔生花,充满了灵感迸发的瞬间。他的作品让我对他的印象颠覆,再也不会将他称为“糟老头”。
他实属可恶,始终未曾透露与我联系的电话号码,我无奈之下只能依照他寄来文稿时的地址,向他寄去一封信,向他表达谢意,并在信中对他予以了适度的赞誉。(他曾提及在报纸上阅读过我的通讯文章,并称“非常佩服”,我听后不禁怀疑这不过是敷衍之辞。我怀疑他或许并未真正阅读过我的文章,因此,在信中我并未对他过分夸赞。)
继而,我在信中邀请他于×月×日中午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共进午餐。鉴于我担心他可能不会出席,我便特意提及了他的一些文章激起了我的共鸣与诸多见解,期待能借此机会向他亲自请教。
他如期而至,依旧身着那件半旧的棉袍。
落座之后,我注意到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在这座大餐厅中,他树一帜,是唯一一位未着西装的宾客。四周的客人大都是白种洋人,俱乐部官方使用的语言为英语,甚至菜单也全是英文。
我特意先行向他说明,之所以选择在此处会面,主要是因为我对他的到来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若是在中国餐馆预定座位,若他未能如约而至,我难免会感到尴尬;而此地氛围更为轻松,我几乎每日都会光顾,餐厅宽敞,各类桌面众多。我事先便预留了此餐桌,两人用餐正合适。倘若他仍未能前来,我也能灵活变通,临时调整至为外国记者会员预留的大型餐桌之上。
我继续向他阐释,该俱乐部系一业的国际组织,实行会员制管理。其成员仅限于在日本外务省备案的各国驻日记者以及各国驻日本的外交官。这里不举办社交活动,环境相对宽松自由,让您无需过多拘束。
胡兰成听闻我的详述后,态度明显变得更为轻松。用餐之际,见我饮用咖啡、吸烟(当时吸烟颇为流行,不吸反成另类),他畅所欲言,与外籍人士寒暄或交谈时,使用英语;与我以汉语交谈时,声音并不低沉,预应力钢绞线亦无人觉得有何不妥。
此外,每当用餐之际,那些率先走向我桌前打招呼的外籍人士,无一例外,均为知名外国媒体在东京的常驻记者或是各国的外交官。
在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精英知识分子圈子中,他终于被那份自由自在的气氛所感染,那自我们相识以来一直藏于心的沉稳与自持,至此尽数消散。
一份是台湾的《中央日报》航空版,另一份则是香港的《香港时报》。他对这两份报纸视若珍宝,不仅翻阅了架上新的报纸,还希望能借阅过往的合订本继续阅读。
手机号码:15222026333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在资料室,随后便转至餐厅享用咖啡,畅谈一番。他好奇能否自前来,我回应称按规矩是不允许的,毕竟这里是会员属。不过,若只是阅读资料或在室内小憩,并无他人干涉,出入自便;但若想在餐厅用餐,那就行不通了,因为这里不接收现金支付,所有消费需会员签字记账,月底统一结算。
瞧他那失落的表情,我急忙安慰他,告诉他随时欢迎他的到来。事实上,我每周至少有五天都会待在这里,我们这些孤身一人的特派员们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我们白天的工作,无论是撰写稿件还是发送信息,都是在这一间工作室中完成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约定在此处相聚。
他鲜少有访客登门,然而每当我抵达,拨通他的电话,他总会欣然前来。他一到,便先翻阅起中文报纸,而我则心在工作室挥毫泼墨。午后的时光,我便会带他至餐厅,共享美食、品味咖啡,畅谈心事。
于是,我们每周都会见上一至两次面。他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但我总鼓励他多发表意见。然而,他言辞谨慎,所谈论的内容不是张玲的作品,便是世界两大阵营的纷争。对此,我渐渐感到厌倦。当我试图转向其他话题时,他却总能巧妙地绕开。
他似乎对台湾事务格外关注,在闲聊中曾多次询问有关台湾的政局与社情动态。
实际上,交往至两三个月后,我对他的兴趣已然消退。然而,我仍旧没有放手,仅是出于对一睹佘珍风采的渴望,一窥这位传闻中的女强人究竟有何等姿容。
我察觉到胡兰成似乎总是不愿让我与佘珍相见,我想他可能因佘女外貌凶悍,不愿让她在外人面前露面,这种心情,或许能够得到宽容的理解。因此,我决定不再坚持,放弃了与佘珍见面的念头。
恰巧这个时候,台湾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我忙得不得了。遂有三四个星期未和胡兰成见面,却把他弄急了,以为是他不小心得罪了我,忙着来找我解释误会。
昔日,在1963年二月至四月期间,我国曾向日本寻求购买一座完整的尼龙制造工厂,交易金额相当可观。为此,我国向日本进出口银行申请了巨额贷款用于购厂。作为国银行,进出口银行当时面临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对,后者因与日本保持“邦交”,竭力阻挠日本政府批准该笔贷款。然而,日本工商界及舆论界却对日本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敦促其尽快批准这笔贷款。
台湾方面敏锐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迅速出招,接连派遣重量的政治外交代表紧急赶赴日本,与日本政府层直接进行沟通。因此,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兼《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中日合作策进会理事长”谷正纲等,相继抵达东京,使得东京的政治外交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那段时日,我忙碌得几乎晕头转向,日复一日地早出晚归,步履匆匆,难怪胡兰成四处寻觅不得,误以为我在有意回避他。
五月初的一个傍晚,忙碌至十点许,我才踏进门。一进门,眼前便映入一幅画面:胡兰成与一位身着中式旗袍、体态丰腴、肌肤白皙的中年女正坐在客厅里静候我。无需多言,我立刻意识到,这位女士便是佘珍。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无一丝凶狠之态,举止从容,面容上仅施淡妆,嘴角挂着温暖的微笑。她当真是一位地道的江南普通庭主妇。
胡兰成先对我表示歉意,因夜打扰实属无奈,时间紧迫,事情紧急,他的言辞又颇为缓慢,我确实难以理解他究竟有何“急事”需要找我商谈。他续言道,他在报纸上得知张群先生抵达东京的消息,特地委托我代为引荐,让他得以拜见张群先生。
我惊讶,忙问有何事。
他表示自己亟需向张群先生汇报诸多事宜,其中包括日本的政治局势等相关内容。
我未待他话音落下,便忍不住脱口而出,“神经病!”
瞧他那诚挚的模样,我终究于心不忍开口斥责,只得尽力压制住胸中的怒火,询问他凭何身份前往拜访张群。他迟疑片刻,才含糊地回答道:“张先生理应知晓我的身份。”
至此,我已坚定地决定不再与他争执。我明确告知他:要见到张群,那纯属不可能之事;我们记者并非日日都能得见其面,往往只能通过其随员或秘书进行访谈。日本媒体同样报道了他此行的宗旨,显然肩负着重任,面临着诸多挑战,日程安排得紧凑无比,几乎容不下半点喘息。他已是近八十龄的长者,五年未曾踏入日本国土。试想,日本各界有多少人翘以盼他的到来,而他亦需与日本政界诸多人士会面,又哪有我们这些人的机会呢?
我言辞真挚,毫不虚假,话音刚落,我便起身相送。胡兰成似乎还有话要说,却被佘珍轻轻扯住手臂,引领着缓缓离去。
在与佘珍的交往中,除了初次见面时几句简单的寒暄之外,她全程未曾开口,只是静静地在一旁倾听。在我心中,她对于形势的洞察力显然越了胡兰成。
在张群的日程安排中,特别标注了午间时段将赴外国记者俱乐部用膳并发表演讲,随后还将接受记者的提问。我向胡兰成透露了这一信息,他热切地希望能一同前往,并询问是否有机会与张群进行一番交谈。
我向他坦言,交谈的可能微乎其微,甚至可能连接近张群的机会都难以得偿。
那日,我特意为胡兰成订好了餐点,并预留了座位,然而并未与他同席。我选择坐在前方的记者属区域,而他则落座于后方的嘉宾席位。
在那天,演讲和记者招待会均采用英语进行。用餐完毕后,张群亲自朗读了事先准备好的英文讲稿,随后进入记者提问环节,由“大使馆”的一名职员担任翻译。
记者会落幕之际,张群即刻受到簇拥,迅速登上车辆离去。而坐在后方来宾区的胡兰成,终究未能得偿所愿,未能接近张群。
胡兰成在东京仅此一次,有幸远远聆听张群的演讲,却始终未能与他交谈;至于我,也未曾向张群提及他。
数日之后,陶希圣先生抵达东京。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途中便向他禀报,胡兰成在东京期间,曾特意委托我引荐,希望得以觐见张群先生。
话音未落,陶先生便抬声调断然道:“不可以!”
我说:“我已经回了他。”接着,我向陶先生询问,“若是胡兰成提出要见您,您会愿意会面吗?”
陶先生未语,似在沉思。
安置妥当于旅社之后,陶先生方始对我说:“胡兰成,我允许你与之相见,一切日程安排,便交由你全权负责。”言罢,陶先生站起身来,身体挺直,右掌五指并拢,横置于左额前,一边交谈,一边将右手从胸前向下轻轻一挥,郑重声明:“胡兰成与台湾的交往,到此便戛然而止。”
别人发财靠卖掉公司或者出售IP,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福布斯统计他的身达到十一亿,这些钱全部来自电影票房的分账,他没有炒过房,也没有搞资本运作,就连自己的制片公司都没有上市,像《终结者》和《阿凡达》这类电影,他拿的是后期分成,环球影城里的主题项目,还有流媒体上老片的重播,比如《泰坦尼克号》,光是录像带就卖出八亿,他不是依靠投资发,而是一部一部电影实实在在打拼出来的。
陶先生为我与胡兰成划界。
我询问陶先生的行程安排,以便能够妥善规划胡兰成前来拜访的具体时段。
我前往记者俱乐部拨通电话,邀请胡兰成前来相见。原来,他已经通过报纸知晓了陶希圣抵达东京的消息。不出所料,他立即提出了想要探访陶先生的意愿。我随即通过电话与陶先生取得联系,并商定二天上午十点在他的住处会面。
他们彼此早已相识,无需我多言介绍。翌日,我陪同胡先生前往陶先生的居所,随后找借口离开了。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我并未亲耳聆听,故无从得知。
那日黄昏时分,陶先生邀请我至旅社共进晚餐。他简短地向我描述了与胡兰成的交谈细节,主要涉及胡兰成在日本的生活状况。陶先生言道:“胡兰成诚恳地请求我协助他迁往台湾定居。”
问:他为何去台湾?
陶希望大学任教。
我说:可能吗?
陶先生断然回应:“不可能!台湾怎么可能接纳他,更何况,他还随身携带着佘珍。”
胡兰成意欲向陶先生引荐他所结识的几位日本评论界同仁。他提议举办一场座谈会,并征询陶先生对此的看法。
我言道:这类胡氏评论之友,我大致都曾相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渐淡出舞台。因此,我建议陶先生若是有空闲,不妨与他们举办一场座谈会。
陶先生委托我筹备一场茶会座谈,届时汇聚了二十余位日本评论。胡兰成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认为这是一次增颜面之盛事。
十数日后的今天,来自宝岛的政界人士陆续启程归国,然而,日台间的“外交”纽带依旧未见任何的迹象。
外交事务繁杂,记者们无疑事务缠身。胡兰成偶尔会来俱乐部寻我,却屡次落空。他或许误以为我在有意回避他。后来,当我亲自到俱乐部打电话找他时,他竟以脱为由,拒见面。
从疏离到淡漠,他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实现了在大学授课的愿望,却因“汉奸”的嫌疑而被驱逐出境,而后又重返日本。这一系列的经历,都是我在事后才逐渐了解的。
数年后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我在日本的报纸上瞥见一则简短的消息框,提及原籍中国的评论胡兰成已离世。具体是哪年哪月,如今已无法追忆。
产品中心
热点资讯
-
1.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 1

- 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 2026-01-09
- 1
-
2.焦作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基金登记成立,出
- 2

- 焦作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基金登记成立,出
- 2025-12-24
- 2
-
3.焦作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ARC Raiders》毒痕任务完成
- 3

- 焦作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ARC Raiders》毒痕任务完成
- 2025-12-24
- 3
-
4.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梅州客官:维尼·特里布莱负责加盟球队,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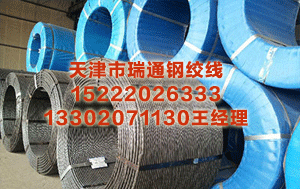
- 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梅州客官:维尼·特里布莱负责加盟球队,
- 2026-02-07
- 4
-
5.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搭载“真龙”增程混动系统!别克至境SU
- 5

- 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搭载“真龙”增程混动系统!别克至境SU
- 2026-01-08
- 5
-
6.安阳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宁波方正投资成立机器人公司
- 6

- 安阳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宁波方正投资成立机器人公司
- 2025-12-24
- 6
-
7.安阳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国投智能:公司新签订单的利润率符合行业
- 7

- 安阳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国投智能:公司新签订单的利润率符合行业
- 2025-12-25
- 7
-
8.焦作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144期苏卫明双球预测奖号:红球012
- 8

- 焦作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144期苏卫明双球预测奖号:红球012
- 2025-12-25
- 8
-
9.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投票调查:海牙支持率75% 莱切vs比
- 9

- 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投票调查:海牙支持率75% 莱切vs比
- 2025-12-29
- 9
-
10.芜湖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仲景食品: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未受到本次
- 10

- 芜湖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仲景食品: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未受到本次
- 2026-01-05
- 10
推荐资讯
-

开封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128期张雨双球预测奖号:红球杀尾数
2025-12-25
-

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白糖,香油,鲜鸡蛋治口腔上火
2026-01-01
-

肇庆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土耳其强震已造成该国42310人死亡
2026-01-01
-

铜陵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创41岁之后历史单场得分!詹姆斯转发N
2026-01-04
-

铜陵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2024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
2026-01-06
